本系列訪談,由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廣州社科院曆史研究所、南方都市報共同策劃推出。
專訪太阳集团1088vip中外關系研究所教授劉永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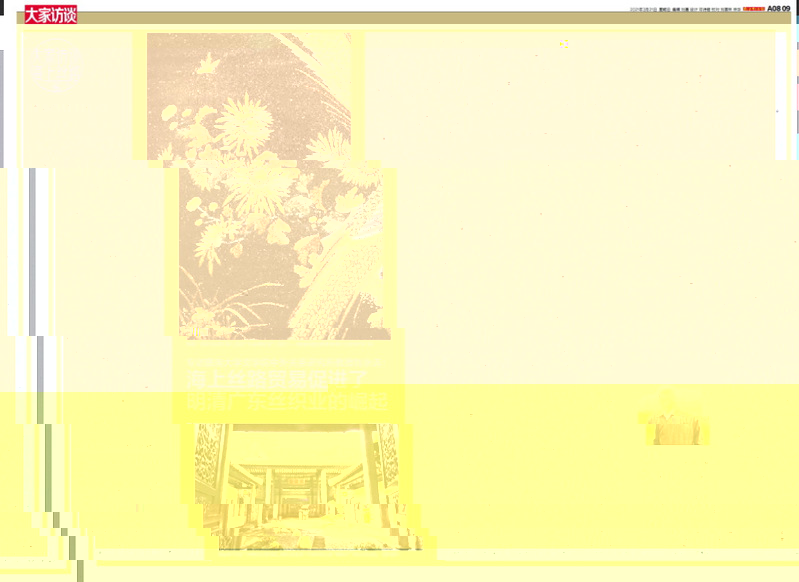
專家簡介
劉永連,男,曆史學博士,現為太阳集团1088vip中外關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長年從事中外關系史研究,尤其關注陸海絲綢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問題。先後承擔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等各級科研項目11項。出版著作《突厥喪葬風俗研究》、《16世紀前的中國與世界》等。兼任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秘書長、理事,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秘書長、理事等。
嶺南海路的曆史作用和地位
南都:在整個海上絲綢之路的曆史上,嶺南海路具有怎樣特殊的地位?
劉永連:首先,嶺南海路在某些表述中指代海上絲路。南海之地是海上絲路的東方路段,是中國向南、向西對外交往的窗口,是中古(3-9世紀)以來中國主要對外交往渠道。北方的空間很小,尤其當陸路衰落之後,主要靠的就是海路,而海路主要是從廣州往南、往西走,所以是中國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廣東的地位比浙江、山東都要重要得多。它對外交往的層面也更豐富,不光有東南亞,還有南亞、西亞、歐洲、非洲,還包括拉美、北美。
第二,因為在海外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使得嶺南地區成為海洋文化特色最為濃厚的地帶。首先,廣東在海外的人最多,有3000萬乃至6000萬華僑之說。此外,廣東的文化習俗和中國北方大不一樣,因為長期和南洋的海外文化交流,形成了比較開放的社會風氣,好多新事物都從廣東進來。特别是到了近代,好多近代化的東西,比方說近代的交通、郵政、貿易等各個方面的新制度、新形式,都是首先從廣東萌芽。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現代經營形式,皆從廣東慢慢往内地發展。可以說,廣東是我國近代化的先行之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泉州定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我覺得廣東特别是廣州人對這件事應該深刻反思。從學術界到政府應該看到,在曆史上廣州對外貿易、對外交往的地位,比泉州不知道重要多少倍。泉州的鼎盛時代僅在宋元時期,也就幾百年。而廣州從秦漢時期一直到近代,一直都是海外貿易的前沿。所以我覺得嶺南海路應該得到特别的關注。
南都:從唐至宋元,廣州港、泉州港等崛起為世界級港口,是否可以稱之為嶺南海路最鼎盛的黃金時代?
劉永連:泉州港以宋元為黃金時代,但廣州發展和繁榮期很長,黃金時代則不限于此。
秦漢時期番禺(廣州)就是天下矚目的大都會,國際貿易繁榮。唐代是一個發展期,被稱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但這還不是最繁榮的時代。明清時期,嶺南的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發展,特别是獨口貿易時期,全國的商品都從廣州出口,這會兒比唐宋時期就更厲害了。鴉片戰争以後,中國給人印象是“落後挨打”,但在實際的海關貿易中,廣州的生絲和絲綢貿易量卻一直在增長。其實,廣州的絲綢外銷,最繁榮期在1920年代。那時候該口岸絲綢貿易量能占到廣東省外貿總額的70%-80%,生絲一項能占到全國生絲出口總價值的40%-50%。應該說,廣州對外貿易的黃金期很長,不限于唐宋元。唐宋是一個大發展時代,明清以降則逐步達到鼎盛,領南海路當與此相對應。
曆史上廣州絲綢外銷的曆程
南都:絲綢是海上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貨品之一。廣州并不是絲織品最大的原産地,從廣州港出口的絲綢大部分來自哪裡?
劉永連:早期,廣州确實不是絲綢的最大産地。不過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在近代特别是鴉片戰争以後,廣州的生絲和絲織業大有發展。一直到1920年代,廣州的生絲生産在全國占到很高的比例。絲綢也有幾十個品種,在海外非常暢銷,在廣州出口貿易貨物中也占據主要份額。
準确一點說,近代以前,廣州等嶺南口岸外銷的絲綢基本靠五嶺以北各絲綢産地的貨物,主要是江浙産區和四川産區。浙江、江蘇一帶,杭州、湖州、蘇州、南京,這些城市絲綢業很早就很發達。從英國東印度貿易文件看,南京産的“甯緞”和湖州産的“湖絲”最受歡迎。四川的絲綢,從長江上遊到長江中遊,然後再通過湘江、贛江到廣州來。北方的山東、河南一帶也有絲綢過來。
自康熙年間起,由于外貿刺激,廣東掀起了一股熱潮,叫“廢稻樹桑”,把水稻田全廢了,用來種植桑樹,嶺南養蠶缫絲業開始獲得巨大發展。康乾時候有一波,到後來道光、鹹豐年間陸陸續續至少有三波這種熱潮。到了近代,廣州基本上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格局,叫“桑基魚塘”,特别珠三角地區,“桑基魚塘”遍地都是。現在去佛山、南海,還能看到許多。鴉片戰争後生絲生産尤其迅速,逐漸支撐起廣州等口岸的絲綢外銷,後來甚至一度超越江浙地區成為全國出口生絲最多的地區。在這個基礎上,廣東的生絲和絲綢業發展很快。外商最早還進湖絲,後來就不進湖絲了,進廣東的粵絲。而且交易量大增,原來就進幾百擔、上千擔,後來最多有十多萬擔。
早于生絲,康熙年間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絲織品就暢銷海外。廣州、佛山一帶形成非常有規模的絲綢生産體系。廣州光是西關一帶就有數萬紡織工人。早期絲織品特别是廣紗優質品要用湖絲加工,後來廣東生絲生産逐步改良和提高,廣紗廣緞等絲織品也就逐漸改用粵絲了。
總之一句話,近代以後,從廣州外銷出去的絲綢貨物基本上就是廣東自産的了。
南都:從廣州外銷的生絲和絲綢被運往哪些國家和地區,利潤幾何?
劉永連:從廣州外銷的絲綢遍及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16世紀起進一步大量輸入歐洲、美洲等地區。因為16、17世紀的時候,歐洲殖民者來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荷蘭人來了之後,歐洲市場随之打開。歐洲在17-18世紀形成“中國熱”,不光是穿絲綢衣服,好多房間裝飾都用到絲綢。歐洲殖民者,尤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又把絲綢帶到了拉丁美洲。再後來,美國、澳大利亞等也逐步加入了對華貿易,絲綢又被販賣到美國和澳大利亞。
絲綢的利潤一直可觀。16-17世紀,荷蘭人從南方沿海販運絲綢到日本,就能獲得數倍之利。根據西班牙人的記述,17-18世紀,廣州絲綢從馬尼拉販運到拉美,通常有1-3倍利潤,最高時可獲10倍之利。
由于影響到國内市場和賦稅,清政府曾經嚴令限制絲綢出口。如在中日之間貿易的商船,會根據帶來黃銅或白銀的數量,來配給多少擔的生絲和絲綢。但限制的僅僅是明面的貿易,走私貿易一直難以控制。
南都:請再簡要談談廣州本地絲綢業發展的狀況。
劉永連:我來說說廣州絲綢業發展的大緻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大概從秦漢一直到宋元,嶺南的絲綢業在全國排不上名次。盡管有人說南越王墓裡有可能是廣東本地産的絲綢。唐代嶺南還出了一個著名人物叫盧媚娘,是刺繡高手,在手絹上能繡《法華經》。古代還有一種“絞绡”,很可能也是南方出産。但是,絲綢業規模沒有形成,這是早期的階段。
明中期至清前期是一個階段,這時候廣東絲綢業突飛猛進。16-17世紀,西方殖民者過來,打開了歐洲、美洲的市場,絲綢需求量大增。由于市場的刺激,廣東的絲織業、随後是生絲業異軍突起。
明朝中葉,廣州有專門的絲緞行、什色緞行、元青緞行、花局緞行、纻緞行、綢绫行、欄杆行、機紗行、鬥紗行等,城内絲織工場達到2500多家。嘉靖年間,則分“蟒袍行”、“十八行”、“十一行”、“金彩行”“廣紗行”等五大行、十幾個小行。清康乾時期,已有廣緞、廣紗等廣東絲綢産品暢銷海外。雍正年間,僅西關一處就有織機一萬多台,絲織工人數萬人。當時著名的絲綢專業會館之一——錦綸會館創建起來,僅其一家會館就統領西關、上下九及十三行附近的數百家大型絲織工場,擁有織機四千多台,絲織工人三四萬人。
第三個階段就是鴉片戰争以後。這個時期,因為五口通商,廣州在出口貿易上受影響了,某些方面不如上海。但在絲綢貿易來說卻是另一個狀态。因為江南一帶的絲綢都由上海出口了,不從廣東出了,所以廣東大力發展本地的絲綢業特别是生絲生産,出口的絲綢逐步過渡到全部依賴廣東生絲來紡織,出現香雲紗等新産品。
明代前期廣東絲織業依賴江浙生絲(湖絲、甯絲),康乾時期起廣東養蠶缫絲業開始發展,道光時期廣東生絲已占出口生絲的一半以上,鹹豐、同治年間率先興起機器缫絲,生絲生産猛增,由此不但可以支撐廣東絲織業需求,而且出口量也躍居全國首位。到了19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東的缫絲已位居全國首位。20世紀初,在珠三角地區從事缫絲業者達三百萬人,絲織工人也有十幾萬人。廣東本地絲綢産品外銷種類、數量也都達到曆史新高度。香雲紗在海内外盛譽尤高。
在近代很長一段時期,絲綢業在廣東社會中舉足輕重,在全國出口貿易中也名列前茅。絲綢業最發達的南海縣,号稱廣東的“銀行”。每天運送生絲和銀元的商船往來不絕。
明清廣東絲織業崛起的原因
南都:是什麼促進了明清時期廣東絲綢業的發展?
劉永連:廣東絲綢業的發展與其他地方所不同的是,它直接以出口為目的。所以促進它發展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國際市場的刺激。明中後期,國際市場發生巨大變化。首先西方人來了,東西貿易勢力交彙,國際市場逐步開拓。16-17世紀,開辟歐洲、拉丁美洲市場;18世紀,拓展至北美、澳大利亞,随後,全球化貿易時代到來。其次,正因為市場開拓,絲綢商品需求膨脹,貿易量空前增加。16世紀末17世紀初,僅廣州口岸就每年出口生絲五六千擔、絲織品40多萬匹。18世紀獨口貿易後廣州絲綢出口繼續一路飙升,至19世紀初僅英國東印度公司統計,就每年出口絲織品七八十萬匹,生絲超過萬擔。
第二,廣東有優越的自然條件。這裡背枕五嶺,面臨南海,處于經濟交流的前沿。同時内陸交通溝汊縱橫,河海相連,具備發達的内外水運條件。再就是廣東處于熱帶,桑樹常綠不凋,每年養蠶能達七到八造,比其他地區春秋兩造在産量上超出很多。特别到了19世紀末,在經過數次“廢稻樹桑”熱潮後珠江三角洲桑基遍地,普遍形成“桑基魚塘”生産模式,由此構成穩固的商品生産基礎。
第三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明清時期珠三角商品經濟獲得充分發展。
明清時期珠三角商業繁榮,資本擴張。1602年,珠三角一帶的墟市(集市)有146個,到了鴉片戰争前夕達到473個。還有商人隊伍。廣東的商人,在明末清初發展到了數十萬人,有幾大幫,比如廣州幫、潮汕幫等等。資本規模也有增長。到了獨口貿易時期,順德商人裡,吳敏、梁玉成、鄧仲豪、鄧仲钊等,皆有數十萬兩白銀資本。當時一兩白銀就是普通人家一個月的生活費用。行商更了不得。比如十三行裡頭伍秉鑒的“怡和洋行”,其資産當時達到了2600萬銀元以上,同文行潘家,資産超過了一億法郎。
商品經濟發展有一個大背景,即國家對外關系從朝貢貿易向私人貿易過渡,同時外貿基調從以奢侈品進口為主向以中國特産出口為主轉化。朝貢貿易偏重政治利益,貿易目的是滿足統治者對奢侈品的需求,而私人貿易是民衆為了經濟利益而開展,由此把絲綢等中國物産作為商品帶進國際市場。在這一背景下,廣州等口岸的貿易不再是過境貿易,而是建立在本地生産發展的基礎上,故而大大促進了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
第四是絲綢産品高度商品化。廣東絲綢以直接出口為生産目的,從種桑養蠶到缫絲織染無不依賴于市場。各個生産環節高度專業化,有專門的桑農、桑市、蠶農、蠶市,缫絲有絲戶、絲廠,外銷的絲行、莊口及孟買莊、金山莊等海外檔口,都是以買賣為主要目的。
有一首《竹枝詞》描繪的是順德一帶的農家是如何與海外市場相聯系的。“呼郎早趁大岡墟,妾理蠶缫已滿車。記問洋船幾曾到,近來絲價竟何如。”早上起來,女的叫男的到大崗墟趕集去,我這兒養蠶和缫絲已經滿了,你記得問問海外的船什麼時候過來,現在的絲價怎麼樣?農家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絲綢生産的商品化是極高的。
還有一點,廣州貿易制度的進步不容忽視。比方說,原來的朝貢貿易,是官員過來管理市舶司。十三行是公行制度,由行商來管。到後來散商起來,就興起了自由貿易,形成了合夥人制度。合夥人制度把外國商人和中國的絲綢商直接聯系起來,如此内外的聯系更密切了。同時興起的還有證券制度、信用制度,銀行、證券、契約,這些東西都出現了,比内地要早上百年。現在說起保險、銀行好像還挺新鮮的,其實兩百年前廣州就有這些事物了。
南都:哪些廣州本地出産的絲織品會出現在海洋貿易當中?
劉永連:到鴉片戰争後,廣州出口絲織品達到數十種。綢類有府綢、線綢、絲綢、水綢、紡綢、素綢、花綢、繭綢、牛郎綢、黑膠綢等;緞類有花緞、錦緞、八絲、粵緞、雲緞、光緞、五絲等;绫類有花绫、素绫、錦绫、線绫、紕绫等。
紗類有直紗、葵紗、夾織紗、包頭紗、銀條紗、軟條紗、軟紗、花绉紗、绉紗、粵紗、線紗、香雲紗等;此外還有畫絹、素羅、絲帶、天鵝絨等許多優質産品。
在各類産品中,廣紗質量最好,号稱“廣紗甲天下”;廣緞中五絲、八絲都是著名産品。屈大均在《廣東新語》裡有一句話:“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鴉片戰争後,“香雲紗”更是作為珠三角特有的絲綢産品享譽海内外。
南都:對于廣州港而言,鼎盛時期的絲綢外銷在海路貿易中占據多大的比例?
劉永連:我這裡有幾個數據。在廣東出口貿易總額中,絲綢貿易價值在鼎盛期達到總值的50%以上,最多的年份(1922、1926、1929年等)超過了80%。民國時期有一個大專家,在美國讀了博士學位回來,專門搞廣東經濟的,他提出,廣東的經濟幾乎全靠絲綢。在那個時代确實是這樣。
還有一個數據,在全國絲綢出口總額中,廣東生絲出口價值達到全國出口生絲總值的40%上下,較好年份可近50%。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北方養蠶絲織一年隻有兩季,分别是春蠶和秋蠶。但廣東因為氣溫較好,一年四季葉子不黃,除了十二月到一月份這一小段,其他時間都可以養蠶。因此廣東養蠶一年最多可以達到八茬,在北方隻有兩茬。所以廣東出産的生絲量非常大。
南都:當時和十三行進行貿易的有哪些國家和地區?在廣州十三行獨攬外貿的時期,絲綢外銷打開了一個什麼樣的新局面?
劉永連:近代的許多外銷畫,裡面很寫實地描繪了十三行的場面。珠江岸邊的十三行:從東到西數,有小溪行(怡和行)、荷蘭行(集義行)、英國行(寶和行)、周周行(豐泰行)、老英行(隆順行)、瑞典行(瑞行)、帝國行(孖鷹行)、寶順行、美洲行(廣元行)、明官行(中和行)、法蘭西行、西班牙行、丹麥行(德興行)。
說起來,十三行針對的是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丹麥、美國等,主要是歐洲國家。當然西班牙、葡萄牙又把絲綢帶到美洲,英國将絲綢帶到澳大利亞。
十三行為絲綢貿易打開了什麼新局面呢?如果從當時商業貿易制度發展來說,十三行确實是一個新發展。原來市舶司時代講的是政治利益,外國使者過來,中國大量賞賜,鞏固政治關系。十三行開始由行商來管理貿易,開始講求經濟利益,要不然就虧本。講求經濟利益,是廣州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再一個,出口商品在朝貢貿易時期控制很嚴,很多貨物在很長時間内是不讓出去的。而十三行管理以後,可以有限制地批量出口。再加上國際市場擴大,絲綢出口量、價值一路上升。這些都大大促進了當時的貿易。特别是獨口貿易時期,即18世紀後半期到19世紀早期,全國各地的絲綢都從廣州出口。
但是我個人認為,也不要把十三行看得太高。因為它畢竟隻是廣州貿易發展中的一個環節。後來的自由貿易階段,尤其是19世紀後半段到20世紀早期,什麼都放開了,廣東絲綢業從生絲到絲織業都發展起來了,大量出口的都是廣東本地的貨物,應該說這一時期對廣東本地貿易影響更大。十三行是廣東對外出口的一個發展環節,但是不是最好的時候。
南都:除了絲綢以外,廣州港在不同時期的海上絲路貿易中還會出口哪些重要的貨物?
劉永連:絲綢以外,還有茶葉、陶瓷、樟腦、姜黃……各種物産及其原料。
南都:你曾經撰寫過《近代廣州對外絲綢貿易研究》和《古錦今絲:廣州絲綢業的前世今生》等著作,是什麼契機讓你将學術研究的着眼點放在廣州的絲綢業和對外貿易上?
劉永連:大概是2000年,廣東省編纂《廣東省志》的《絲綢專志》,編者找到了我。我當時很痛快就接下來了。《絲綢專志》貿易史那一塊就是我做的。我原來是搞唐史、西域史的,因為這個契機,我開始關注廣東絲綢業和海上絲綢之路。
作為教師,除了上課、寫書、做學問之外,也要接觸社會。我和廣東省絲綢集團總公司的謝汝校先生等人是老熟人,這一二十年裡我們經常聯系,曾為深圳“中國絲綢文化創意園”出謀劃策,也考察過順德的絲綢博物館、廣州的錦綸會館等地方,還參加過佛山市政府組織的紀念陳啟源和探讨桑基魚塘文化的會議。學以緻用吧,死讀書有什麼用呢?把自己學到的東西讓别人知道,了解曆史,也是我的一個初衷。
再一個,在廣東讀書、工作、生活,當然要為廣東服務。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南都:從唐代廣州港的崛起到清代廣州十三行的一枝獨秀,海洋貿易給廣州這座城市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劉永連:首先,使得廣州商業發達。因為廣州近代貿易的發展、改良,基本都是從絲綢開始的。比如我說的合夥人制度、信貸制度,許多新興制度都是從絲綢貿易開始的。
其次,促進了城市繁榮。現在全國一線城市廣東占了兩個,這不是偶然的。廣州的繁榮可以說是由來已久,而且有很多曆史記載的。
再次,是廣州高度國際化。廣州在唐代就有十幾萬的外國商人居住,這是國内好多地方不能比的。
最後,上升到人文層面,廣州的文化特色是兼容并蓄,包容性強。因為對外交往多了,大家見識廣了,中外文化都能吸收和擁有,對外來人和事物也能坦然容納,這也造就了廣州這個城市強大的生命力。廣州有很豐富的地域文化。所以我一力主張,廣州應該把地方文化給挖掘出來,給張揚出來。
南都:在海交史領域,未來你還有什麼研究計劃?
劉永連:我最近出的一本書就是《東亞海域和古代中國》,東亞海域也包括南海。以此為視角來觀察中外交往和關系,可以發現許多有趣的東西。
未來海上絲綢之路仍然是我研究的重點。首先,繼續深究海上絲綢之路重大問題,如目前在研的“明代海上回回商旅問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項目),還有如何從宏觀和局部聯系來提升對絲綢之路網絡的認識,等等;其次,把東亞海域作為關注的重點,探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交往、民間和地方力量在東亞海域的活動等;最後,立足嶺南之地,繼續探讨以陸海絲綢之路為視野的中外文化、經濟交流等問題。
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
原文鍊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21-03/21/content_498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