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楚旋

彈幕、丁真、凡爾賽文學……談話間,屢屢提起這些網絡熱詞的,不是社交媒體的網紅博主,也不是二十出頭的網絡潮人,而是太阳集团app首页中文系副教授、文藝學教研室主任鄭煥钊。
學校附近咖啡廳裡,鄭煥钊留着利落寸頭,戴着黑框眼鏡,儒雅随性,看起來僅比周圍的學生略顯成熟。他正對着筆記本電腦沉思,為一篇篇網絡文藝評論的稿子打分。這項尚未完成的工作,他昨晚評改到了深夜。
雖是一名“青椒”(青年教師),近年來鄭煥钊在文藝理論和評論路上屢結碩果,在《文藝研究》《人民日報》等重要報刊發表學術論文和文藝評論近50篇,入選中宣部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廣東省第十一屆“新世紀之星”,獲得“中國文藝評論最高獎”——首屆“啄木鳥杯”文藝評論年度優秀文章獎。
盡管如此,鄭煥钊虛心說到,自己的文藝理論和評論道路剛剛起步,唯有鞏固好思想文化之“根”,求真務實、勇敢解剖問題,才能讓文藝評論始終葆有銳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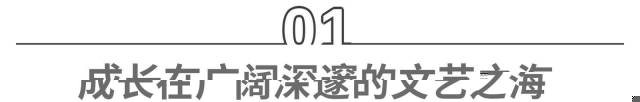
出生在潮州鄉村的農民家庭,鄭煥钊從小對文化從不“挑食”,書籍的匮乏使他凡是能拿到手的,不管是經典作品還是通俗小說,都如饑似渴“一窩蜂地接受”。“偷塞一兩本小人書在身上,趁農活間隙在草垛上閱讀”,正是他童年最快樂的時光。
1990年代初,鄰居同學家購置了電視機,他經常“光顧”,把當時能看的動畫片、影視劇、甚至是潮劇等各種文藝内容都看了個遍。常常看得入迷忘了回家,直到母親在巷子裡喊他吃飯,才戀戀不舍地離開。
看得很“雜”,讓鄭煥钊養成了寬泛的興趣,他對文化的雅俗并無偏見,對各類大衆文藝都持有一種好奇與“同情式理解”。這段經曆也讓他後來能夠以較為客觀的姿态對各種文藝形态和思潮進行研究。
 鄭煥钊(左二)和學生
鄭煥钊(左二)和學生
鄭煥钊從小學習努力、成績優異。從潮州著名的金山中學畢業後,考入太阳集团app首页中文系。在這裡,他首次接觸到令他倍感新奇的文藝理論和文學經典,比如福柯、後現代主義、米蘭·昆德拉、博爾赫斯等。
“嶄新的藝術表達方式給我帶來極大沖擊,全然不同的思考角度讓我越看越着迷。”鄭煥钊回憶。當時,他常與要好的同學讨論共學,有時還特意到其他大學旁聽哲學講座。
大學數年,鄭煥钊打下了堅實的文藝理論基礎,并留在暨大先後攻讀文藝學碩士、博士學位。“太過具體的學科,可能會限制我的研究興趣。”暨大文藝學注重面對現實批評,具有跨文化研究的學科傳統,正契合他廣泛的閱讀興趣與研究期待。
 鄭煥钊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合照
鄭煥钊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合照
鄭煥钊的碩博導師蔣述卓曾如此評價:“他比較特别,在本科階段就頗受老師重視,活躍的思維和紮實的功底,讓給他上過課的老師都記得住他。”
近十年的求學生涯,最難忘是師者諄諄教導。鄭煥钊告訴記者,早在本科期間,他就接觸了暨大中文系饒芃子教授的著作,從中“獲得了對文藝理論和批評寫作的真正啟蒙”。饒先生以女性學者“體己式”的睿智與風度,更讓鄭煥钊産生了對學術職業的向往。
“饒先生立足中華文化之根,以跨文化比較的視角,開辟了比較文藝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的新領域,這種學術方法論讓我深受啟發。”令鄭煥钊記憶猶新的是,饒老師曾認為他的文字“很老道,超脫了青年學者的稚嫩”,這對他的學術成長起到了重要激勵。有時,同樣來自潮州的饒先生還會親切地稱他為“小老鄉”。
碩博五年,鄭煥钊師承暨大中文系蔣述卓教授。蔣教授以其宏闊的文化視野、深厚的學術積澱,在課堂課外引領學生閱讀文藝理論經典,輔以高屋建瓴的精辟講解,引導培育學生對文化的現實關懷。
“蔣老師直接面對當下問題、注重以跨學科的文化視野探求現象産生的内在機制的研究方法深深影響了我。”求學期間,他積極參與導師承擔的多個課題,如《傳媒時代的文學存在方式》《流行文藝與主流價值關系研究》等,“正是在跟随老師研究的過程中,培養了我探究新現象新問題背後的新經驗與新機制的興趣與方法。”

2012年,鄭煥钊完成學業,成為母校暨南園裡的一名青年教師。在課堂上,鄭煥钊深得學生喜愛,被譽為“男神級”老師,他在暨大首設的《文化産業與文化管理》課更是常年爆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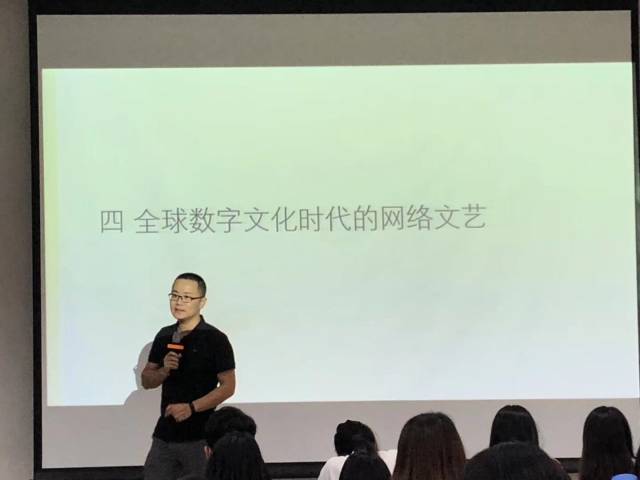 鄭煥钊講授課程
鄭煥钊講授課程
“剛參加工作時,前三年很難展開學術研究工作。”鄭煥钊告訴記者,當時他同時承擔了三門課程,為彌補經驗不足,他盡量多地備課,每周近乎用去全部時間。而備課也非一勞永逸,每輪教學後都需要不斷進行新的調整。
所幸在研究生時期,無論多麼忙碌,他已養成每天閱讀文獻的習慣,并保持高強度的工作效率。至今,他已執教近20門不同的課程。
為兼顧教學、科研與評論,鄭煥钊的辦法是“盡可能多維度地觀照文化文本”——同一個研究對象的調研分析,既能成為課堂教學的案例,也是開展研究的素材,亦能成為發表批評的工作基礎。
 鄭煥钊參與主編或著述作品
鄭煥钊參與主編或著述作品
“高校學者的優勢在于,對新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分析論證時,已經具備了較為成熟的方法論。”在他看來,人文學科讓他獲得“對人的深入理解的能力”,強調在一套複雜的社會和文化系統中,把握人的命運、理解人的選擇、感受人的情感,這與文化産業理解消費者的情感需求和消費選擇,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因此,從人文學科基礎理論的研究到文化産業的政策調研,似乎相隔很遠,但鄭煥钊認為其方法論其實是相通的。

工作步入正軌後,鄭煥钊逐步承擔起越來越多的文藝評論工作。2016年,中國評協在暨大召開的一場網絡文藝座談會上,鄭煥钊将其觀察撰寫成《網絡文藝的形态及其評論介入》做了發言,得到廣泛認可,并發表在《中國文藝評論》上,初試牛刀。
半年後,另一個喜訊傳來——他憑《國産動畫價值取向和表述的誤區及其突破》獲得首屆“啄木鳥杯”文藝評論年度優秀文章獎,被評價為“展現了一個青年批評家對藝術之中蘊藏的‘大義’之持守,以及獨到的眼光和學術銳氣”。

從如雲高手中脫穎而出,鄭煥钊非常意外,也倍受鼓勵,讓他堅定了“勇敢、誠實地進行批評”這一信念。此後,鄭煥钊成為廣東省評協理事之一,被中國評協、廣東評協共同推薦參加數屆中國青年文藝評論家“西湖論壇”,這些平台讓他在文藝評論道路上得到較好成長。
回想起這篇獲獎文章的誕生,最難忘懷的是那3個月的全心投入。在沒有課的晚上與周末,他夜以繼日地閱讀文獻,擠出時間一遍遍地“審閱”動畫片。
“作出切中要害的評論,是非常艱難的過程。”鄭煥钊說,首先要對該領域持續深入觀察,方能“打磨”出一個歸納精準、普遍存在的“好問題”;其次,要想找到合适的分析方法,這就需要深厚的藝術理論積累,即在動畫發展史、動畫藝術特征、國内外藝術比較等方面“補課”;經過邏輯嚴密的論證、推演,最終提出獨有的創新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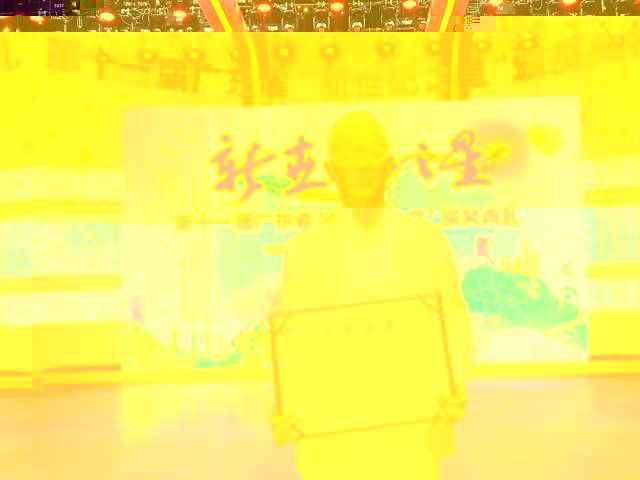
“任何一個問題的探索,都充滿着焦慮和痛苦,是不斷遭遇挫折的過程。而一旦‘想通’了,就會獲得無與倫比的成就感。”文藝評論在高校科研中并不被重視,因此他偶爾也吐露“愛好與工作融合”的艱難與苦悶,但他也漸漸掌握兩者平衡的技巧,堅定攀登文藝評論事業的無盡險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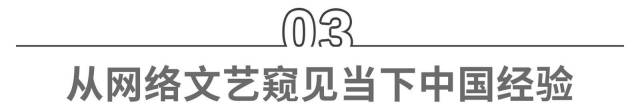
近年來,在互聯網熱潮席卷文藝領域的當下,鄭煥钊常常忙得不亦樂乎:“追”最熱門的影視劇作、“評”新出現的文藝現象、“教”不斷更新的學科内容、“研”日新月異的文化問題。廣州市重大社會風險評估專家、廣州動漫協會顧問等多個社會兼職,正是對其行業敏銳度、掌握力的充分證明。
如今,來自《人民日報》、《文彙報》、光明網等媒體的約稿和采訪不斷,邀請鄭煥钊對當下熱門的影視綜藝新現象進行讨論、分析、點評,如“彈幕”是什麼、“凡爾賽文學”為何出現等等,在業界頗受好評。康巴少年丁真爆紅初期,鄭煥钊應邀展開讨論,由于把握及時,相關評論文章得到廣泛轉載。

“研究網絡文藝背後的複雜生态,可以窺見當下中國經驗的呈現方式與文化邏輯。”鄭煥钊認為,在技術賦權與資本參與下,互聯網時代文藝創作、傳播與接受呈現出了嶄新的經驗,多樣化的文化形态及其參與方式,使網絡文藝超越單純的文藝問題,必須從政治、社會、技術和産業等多個維度,對其演變曆程、内在經驗和存在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嚴肅探讨它們與社會的複雜關聯。
在此背景下,評論者介入現實、引導行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鄭煥钊主要從文化治理的角度對當前網絡文藝及其産業進行批評研究,通過對網絡文藝新文化、新文藝形态的全面清理,從批評理論上提出要從創意批評和生态批評的角度進行研究,并從社會學的層面讨論網絡底層文藝發生發展的邏輯,關注網絡文藝中底層大衆的文藝參與對中國當代文化格局所帶來的影響。
“新的文藝思潮來臨,文藝評論必須到場。”省評協主席林崗曾指出,許多年輕人關注的熱點作品,往往是傳統評論家較難及時、準确把握住的領域,需要對新文藝體裁有新銳思考的新一代評論人才。

鄭煥钊深知,中文系課堂并不直接培養評論人才,因此他采取“有意識引導”的方法,注重對學生文本解讀、辯證分析的訓練,讓學生形成對當下文藝的判斷勇氣與評價标準。
“文藝評論本質是對文化的評價、分析能力,不僅用于撰寫評論文章,在往後從事文化生産、傳播的過程中,也能發揮價值引領的作用。”他認為,無論是否從事文藝評論工作,這種獨立思辨的能力都将使人受益終生。
文章來源:https://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106/12/c5404240.html?colID=12722&firstColID=12722&appversion=7710&from=timeline&date=ZjM0NzgyYmItN2VlNC00MjA0LThkZjItY2JjODI3YjkwYTQy&layer=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