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指出必須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産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
在暨南園,有這樣一位老師,深耕于中國文化史籍研究領域20餘載,沉潛曆史深處,默默堅守,傳承文脈;在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同時,重返曆史現場,超越空間限制,突破古今隔閡,同情并理解古人的文化精神,真正緻力于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讓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活起來。”他,便是太阳集团1088vip副院長、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王京州老師。

(王京州教授)
一、初心如磐:涵養讀書治學“願力”,成就不懈奮進之路
“成為一個知識淵博的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中學時代的王京州,在日記簿上端端正正地寫下這句話。
知識淵博,是從外到内的汲取;對社會有用,是自内向外的回報。少年時代的夢想成為王京州立身行事的初心,一路走來,他以實際行動不負少年鴻鹄志,現已成為中古文學典籍研究領域知名學者,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王京州看來,自己仍腹笥貧儉,距離學識淵博還差得遠,需要以此初心不斷鞭策自己努力讀書,活到老學到老。
北京大學廖可斌先生在《讀書三力》的演講中所講到的第一力是“願力”。“願力”也可稱作“信力”“意志力”,它是讀書治學的基礎,決定了讀書治學成就之有無。王京州認為,“三力”這一箴言具有普遍意義,不止适用于讀書求學階段,“在一位學者的一生中,時刻都會面臨‘願力’持續的問題。”
王京州的讀書治學之路并不是一條坦途,但他卻有着堅定的“願力”。高考成績不理想,他便毅然選擇了二戰,最終考取四川大學。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天資出衆的人,本碩期間表現出色的同學大有人在,但他們大多在畢業後離開了學術領域,而他選擇了潛心治學并堅守于此,“學術道路注定是寂寞的,隻有少數人才能走得更遠”。
“遠徙的初衷,是想要成為更好的自己。”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王京州回到家鄉的小城,在一個學院圖書館裡任職。他坦言,這一年他的精神是異常苦悶的,“似乎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将自己拖拽着、撕扯着,陷進世俗庸常的車輪”。但他沒有聽任它的擺布,而是通過近乎瘋狂的閱讀和學習與之對抗,最終成功考取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苦悶與荊棘的背後,是鮮花與碩果的回報。在河北師範大學太阳集团1088vip就職期間,王京州成功獲評教授頭銜,他幽默地笑稱自己本可以就此“躺平”,但他并沒有被舒适圈的誘惑阻攔腳步,奮鬥不息的“願力”再次推動着他接受更大的挑戰——離開家鄉,前往廣州,成為暨南園的一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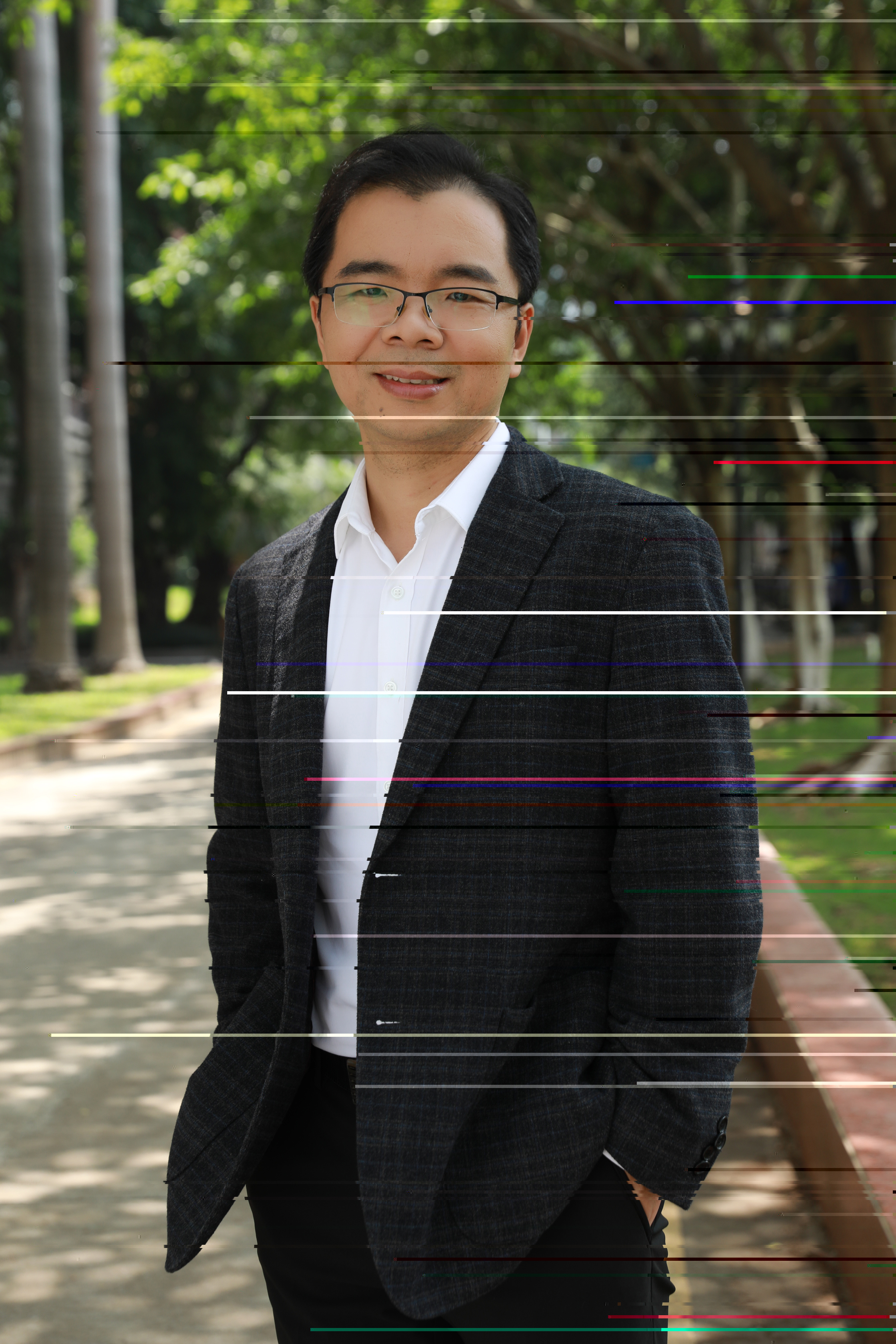
(在第一文科樓前)
二、潛心治學:深耕中國古典文獻學,結緣類書研究
“中古文學典籍是不朽的,對當代文化精神的建構有着重要的價值。”
王京州曾系統整理齊梁時代陶弘景的文集以及明人張燮對于漢魏六朝七十二名家作品的評論集。陶弘景是一位在宗教、科技、中醫、文學、書法等領域均有創獲和貢獻的名家,他在政治上激流勇退,退隐山林,卻并未忘情于人世,仍然指點江山,人稱“山中宰相”。此外,王京州還涉獵過曹植、阮籍、嵇康、陶淵明、庾信等人的詩文集,他們至情至性,疾惡如仇,風骨剛健,然而卻不得不與世沉浮,在現實中不得志,轉而寄情于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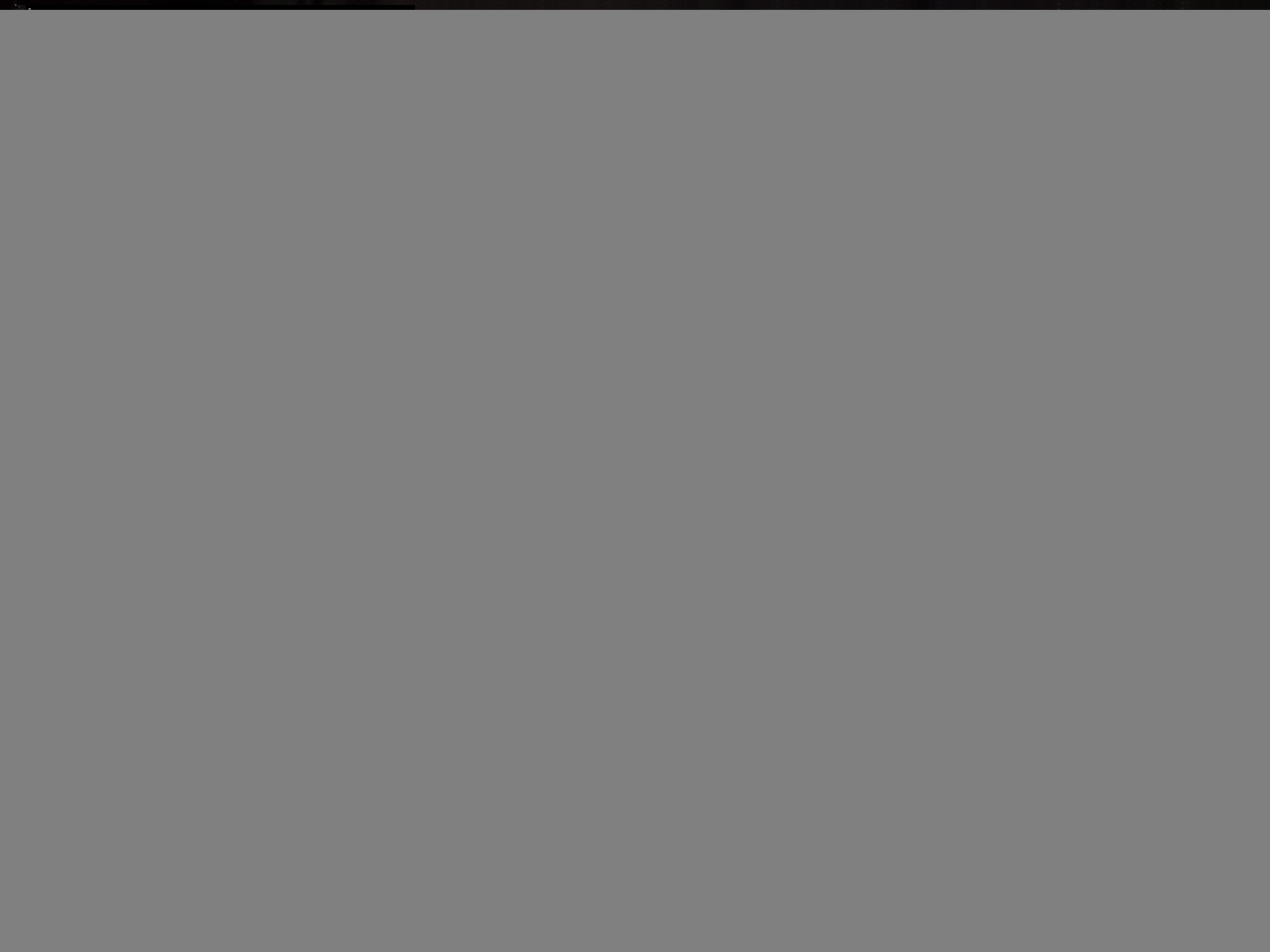
(部分著作再版圖影)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也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然而由于時代久遠,戰亂頻仍,大部分作家的文集都亡佚了。”明人張燮肆力于整理漢魏六朝作家文集,并對這些作家的為人為文分别作了凝練的評價。在研讀和整理張燮題辭的過程中,王京州對漢魏六朝文學和那個時代的心靈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時也熏陶、建構了自身心靈。
提及與類書研究結緣的契機,王京州談到他在四川大學讀書時,曾有幸追随著名的龍學大家楊明照先生,擔任楊先生晚年的資料助手。楊先生曾讓他抄錄《彭氏類編雜說》中引用《文心雕龍》的資料,并指導他撰寫過一篇介紹《彭氏類編雜說》的短文。“這篇稚嫩的文字後來發表在《成都大學學報》上,這也是我發表的第一篇與學術有關的文章。”
《彭氏類編雜說》恰好是一部類書,一部明人私編的類書。類書号稱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其實也是古代辭書的獨特形式,是供古人查檢文獻資料的淵薮,可以視為中國古人的搜索引擎。由于保存了大量後世失傳的文獻資料,類書産生了始料未及的文獻價值。在王京州看來,“即使在進入大數據時代的今天,類書的文獻價值并未削弱,尤其是對古典學術研究來說。”
在羅國威先生的指點下,王京州的碩士畢業論文以整理《陶弘景集》為題。由于陶弘景的作品已經散佚了,而類書中保留了一些殘圭斷璧,所以經常要使用《藝文類聚》《太平禦覽》等唐宋類書進行輯佚,王京州也由此對類書的價值産生了更深切的理解。
後來,他與同事一起參與了當代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華大典》這一部超級類書的編纂。在種種機緣際會之下,王京州更加關注《北堂書鈔》《初學記》等著名類書,内心想要整理研究類書的願望愈發強烈,由此成就了他以類書研究為題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重大項目的契機。

(線上主持古籍研究青年論壇)
三、薪火相繼:赓續前人學脈,喚起精神共鳴
漫漫求學路,悠悠恩師情。
王京州本碩和博士階段分别就讀于四川大學和南京大學,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對王京州産生影響的人和事有很多,其中影響最大是四川大學的羅國威老師。“羅老師一直以來的激勵和愛護,是我學術道路上永遠的燈塔。”
此外還有許多恩師都在王京州的求學之路上産生深刻影響,如四川大學的楊明照先生、南京大學的程章燦老師和鞏本棟老師、北京大學的廖可斌老師等。“這些學者都來自南方,加之我現在寄寓嶺南,可以說我雖然是北人,但流淌的一直是南方的學脈。”
當王京州博士畢業,回到河北故土後,他作為北人的根性又被激活,内心質樸的鄉梓情懷指引着他尋找現代學術史上的河北學者。
他通過編校年譜的方式,細數那一代學人的生命年輪,發掘他們的學術精神,品讀他們獨特的學術曆程,形成了《北望青山》中的“讀年譜”文章系列。這既是向那一代學人緻敬,同時也将他們的精神内化為自己學術生命的一部分,“他們的生命琴弦都曾引起我的共鳴,他們的堅守也是我的堅守,欲罷不能;他們的塊壘也是我的塊壘,不吐不快。”
《北望青山》重點寫到的近三十位學人,均已作古,但他們奮鬥的足迹并未消失,他們的精神仍以不同的形式影響和激勵着王京州。
當分析顧随先生所面臨的三次重要人生抉擇時,王京州自己也正面臨着人生中的重大選擇,即是否南下;胡如雷先生在命運撥弄與時代影響之下,不得已而身處于一個完全沒有學術氛圍的環境,但他仍不放棄,尋求突圍,這讓有着相似工作經曆的王京州感同身受;夏傳才先生在退休年歲才開啟學術生命,仍取得輝煌成就,雖卧病在床但精神極為健碩,對前來探望的學生熱情、悉心指導,這一形象永遠定格在王京州的腦海之中。

(《北望青山》書影)
人文科學精神代代相承。王京州所從事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屬于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看似有着巨大的鴻溝。但在他看來,無論是探尋一個字的古義,考證一本書的作者和時代,還是盡可能恢複古籍的本來面貌,在求真求實這一點上,古籍整理和中國古典文獻學是與自然科學胎息相通的。進而來說,自然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也應該是相通的。著名科學家竺可桢說,科學精神就是“隻問是非不計利害”,科學家的态度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當然也适用于人文學科。
唐代大學者韓愈說:“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黃海章先生和王運熙先生都不約而同地以韓愈此言勉勵弟子,吳承學先生也常常把這句話轉贈學生們。王京州在捧讀吳先生《冰壺秋月》一書時,對這一傳統的遞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将之視為人文科學精神的薪火赓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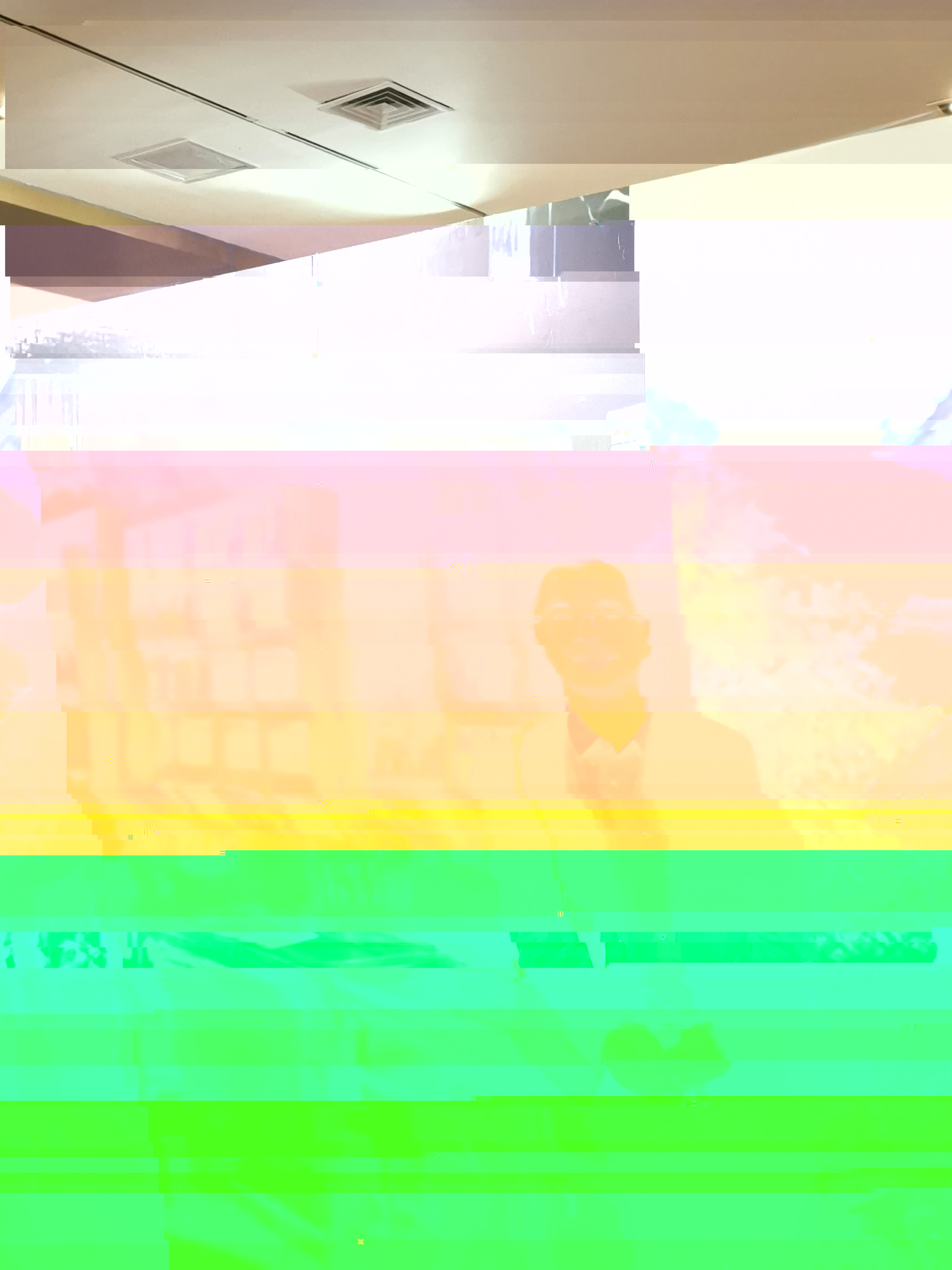
(在中山圖書館古籍部)
四、任重道遠:為後輩立标杆,為時代擔使命
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對教師來說,想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的人,自己首先就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句話久久響徹于王京州的腦海。
從向宗魯先生到楊明照先生,從楊先生到羅國威老師,再從羅老師到王京州,在校雠學的魅力與學術傳統的影響之下,王京州走上了古籍整理事業的道路。在參加廣東省首屆本科高校課程思政教學大賽時,王京州特别設計了一個教學節段,題為《薪火赓續:向宗魯、陳垣與校雠學派》,将自己在太阳集团app首页的課堂嵌入到了這一學術史薪火相傳的脈絡之中,以“傳承文獻經典,赓續中華文脈”的課程思政理念取得了大賽文科一組第一名的佳績。

(在課程思政教學大賽上)
在自身受此學術傳統感召的基礎上,他自覺自發地将其發揚光大,引導着更多的青年學生走上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道路。
依托太阳集团1088vip本科生“國家社科基金助研計劃”,王京州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優秀學子。他們在王京州的影響下,對古籍研究産生了濃厚的興趣。王京州還通過主辦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論壇、延請業師羅國威先生來穗講學等方式,讓同學們接受更多的熏染。

(羅老師講座與弟子合影)
如今,已有多位學子走上了古籍研究的康莊大道,如鄒逸軒、李思怡、李露薇等,他們将要或已經暫時離開暨南園,到複旦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等知名學府負笈深造。王京州對他們寄語道:“古籍整理和文獻研究是寂寞的,但卻是有意義的,值得我們為之不懈堅守。”
談及使命,王京州可謂重任在肩。在他看來,作為一名教師,他的使命是教好書,讓學生真正獲益,“傳道、授業和解惑,這是為人師的職責,每一項要完成得好都極為不易。”而作為一名學者,他的使命是通過古籍深度整理的方式,更好地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這一方面,有太多的計劃等待完成。”在教師和學者的使命之外,王京州還任太阳集团1088vip副院長,分管學院本科教學工作,“擔負着文史人才培養和規劃的責任,這一方面同樣任重而道遠”。
文/康清越 肖潇
圖/王京州老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