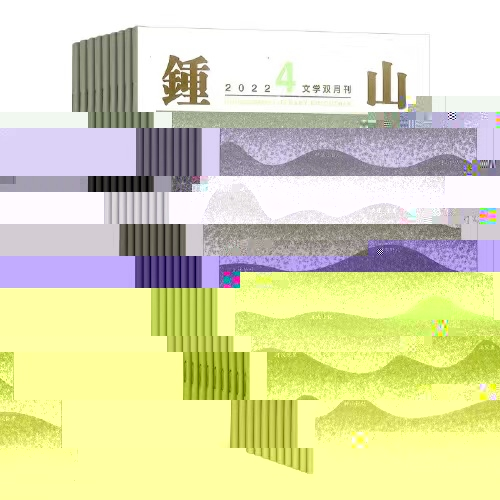
馬拉《托體》
原刊《鐘山》2022年第3期
選載《小說選刊》2022年第7期
作家●介紹

馬拉,1978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在《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等文學期刊發表大量作品,入選國内多種重要選本。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餘零圖殘卷》等五部,中短篇小說集《廣州美人》等三部,詩集《安靜的先生》。
讨論《托體》
主持老師:唐詩人(太阳集团1088vip副教授)
讨論成員:太阳集团1088vip本科生鐘耀祖、朱苑盈、鄭涵、梁恩琪、區采婷、紀亞昆
本期導語唐詩人
每次讀馬拉的小說,都會瞬間被他獨特的叙述帶入一種奇怪的狀态。說實話,我個人不太喜歡這種狀态,他的講述他主觀了,就像現場聽他說話一樣,他剛開始講我就知道他要開始瞎編了。但真等他開始說開來,又很願意聽他繼續扯下去。他講,我隻負責聽/看,聽/看完感慨唏噓一下就好。這種“欲拒還迎”的閱讀感受,獨屬于馬拉小說的叙述風格。因為這種狀态,我一直都不太知道該怎麼來談論馬拉的小說,我隻想對他講的故事點個贊、喝個彩,要當個評論家來長篇大論說點什麼真難為人。這種感受,在讀他的中篇小說《托體》時更為突出。
《托體》的“托體”,來自陶潛《拟挽歌辭》,“托體同山阿”,開篇架勢十足,想着馬拉要嚴肅起來了?但一句“吾友老譚”又露真面目了,馬拉還是這個馬拉,開始說故事了……不過,這個故事的确嚴肅了點,馬拉故意把自己編進去,且刻意不讓故事變得“圓滿”:易過庭沒找到他的兒子,他老婆趙曼生就病逝了。但比父子、母子相認這樣的“大團圓結局”更“圓滿”的是,這個未能找到的、作為入殓師的兒子,在馬拉的安排下為自己未相認的母親化了最後的妝容。世事難料,命運捉弄人,太讓人唏噓。馬拉怎麼能這樣呢,怎麼就不願意讓這個母親死前見一眼兒子呢?即便安排這個母親死後送到了殡儀館,在接受親生兒子最後的化妝時又醒過來,讀者也能夠理解這份詭異吧……正經點說,馬拉不願落入俗套的叙事,才真正引人慨歎: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本期召集了太阳集团app首页六位本科生,且看他們的正經評說。
點 評
半掩在生活中的“荒蠻故事”
鐘耀祖(太阳集团1088vip本科生):
馬拉的中篇小說《托體》中存在兩種叙事模式,其中一種沒有明顯的矛盾沖突來構成推動情節發展的動力,也缺乏連貫的線索,顯得雜多松散,類似散文叙事,可以稱之為“散文性叙事”,小說中的“小引”、“鐵城歌謠”、“補遺:想象或虛構”大類如此;另外一種有明顯的矛盾沖突推動情節發展,有連貫的線索,情節集中緊湊,屬于常見的小說叙事,便與“散文性叙事”相對應地稱之為“小說性叙事”,小說中的“荒蠻故事”便是如此。
小說共有四章,其中的第二部分“荒蠻故事”主要講述了一對中年企業家夫婦的故事。妻子趙曼生身罹癌症,吐露出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一氣之下棄養兒子的實情,丈夫易過庭得知自己還有兒子,又驚又喜,便赴“鐵城”尋子,還托了朋友祁新聞幫忙,久久未果。最後,趙曼生病逝,小說則暗示那個為她遺體化妝的青年入殓師孟一舟便是她當年棄養的兒子,而他當時又正好是邝新聞的女兒邝詩雲的戀人,如今天人兩隔,母子就此錯過相認的機會……這部分運用了巧合、突轉等叙事技巧,情節集中而富有張力。而小說其他部分的叙事則在整體上給人一種“拉雜成篇”的感覺,就像酒過三巡後作者在酒桌旁邊跟讀者聊起生活中的奇聞轶事:這些部分以“我”、“老譚”的視角來講述諸多人物的往事和生活經曆,表現這些人物或懵懂或苦惱或偏執或透徹的生存狀态和精神面貌,比如老譚在鐵城殡儀館工作的随緣自适,易過庭對妻子的微妙感情,朱鼎文對子女教育的執着,邝新聞對于女兒執意要與殡葬師戀愛的煩惱,孟一舟對于養母感情的猶疑與釋然……這些雜多的生活體驗随着人物的接觸交往而交織在小說之中,呈現出百味陳雜的人生百态。而易過庭夫婦尋子的情節線索在這些蕪雜散漫的叙事之中若隐若現,有如草蛇灰線,但作者抽掉了巧合所帶來的戲劇性,将懸念揭開時的情節幾筆帶過,結尾又回到了對于“我”、“老譚”等一衆朋友聚會場景的叙事之中。
這樣,最富有戲劇性的情節被冷落,被淡化了,瑣屑枝蔓的“散文性叙事”幾乎都要掩蓋住了其中“小說性叙事”,故事的戲劇性被消解于日常生活叙事之中,而這一點恰好體現了一種書寫現實的觀念:現實本身就是現象與情感的雜多堆積,那種集中緊湊的情節隻不過是小說家有意裁剪的結果。而《托體》這種叙述現實雜多事件的“散文性叙事”,便體現出追求書寫生活“原生态”的味道。從另一方面來看,充滿了偶然性的現實也會産生不少戲劇性的事件,“小說性叙事”的戲劇性寓于“散文性叙事”的生活性之中,馬拉《托體》裡的“荒蠻故事”,就有如半露于地表的化石,在生活瑣屑塵土的遮掩下,隐隐顯露出其猙獰的輪廓。

在現代文明社會中解決荒誕的人情羁絆
朱苑盈(太阳集团1088vip本科生):
台灣作家袁哲生有一篇同樣是寫殡儀館的短篇小說,裡面寫道:“死亡就跟對發票一樣,早晚會中獎的。”死亡是很多作家繞不開的終極命題,也是當代先鋒作家在時代叙述中對于傳統死亡書寫進行反思和超越的典型對象。
“托體同山阿”,《托體》文如其題,在大量人情世故的鋪排和略顯俗套的臨終尋子情節後,向讀者不急不緩地提出了如何在現代文明社會之中,去解決荒誕的人情羁絆、處理生與死的沖突,最終完成生命最後一程得以安放肉體的叩問。
馬拉用看似繁蕪閑雜、信馬由缰卻又精彩十足的筆墨,将幾位有着迥異的性情志趣和人生哲學的鐵城人、幾個各有偏見或糾葛的家庭、幾個江湖氣息各異的圈層(包括商業圈、文藝圈、學術圈等)、幾組在暗中環環相扣的尋找和沖突,拼接為一個簡明而不失懸念、怪誕而不失真實、深刻而不失幽默的大故事,刻畫出人類對于生命與人情的普世思索和困境,芸芸衆生世俗生活的酸甜苦辣百般滋味,以及生與死之間并不神秘的愛的流動。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在叙事手法和形式結構上也有着獨特的創作力。例如隻在“小引”和“補遺:想象或虛構”中出場的“我”,時而公開時而隐蔽的叙述者将對情節、人物的現實審視和哲學思考引到了有趣的位置;結尾設置巧思妙想不着痕迹,在透着黑色幽默的“酒後真言”“臘豬腿閑筆”之中讓讀者心甘情願地踏入“騙子”作家的故事圈套,發人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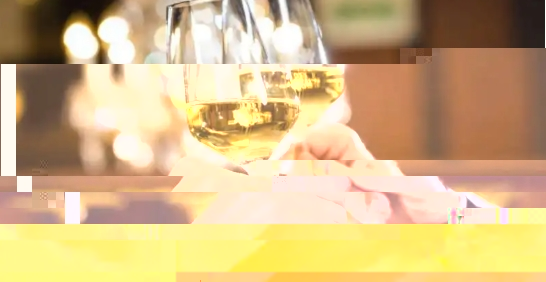
死亡——平常的不可說
鄭涵(太阳集团1088vip本科生):
小說對于世俗對殡葬工作人員的态度描寫是細膩而又真實的。身為生命歸于黑暗、飛向虛無之前最後的守護者,殡葬工作人員細心地呵護着逝者在人世間最後的尊嚴,也關照着親人對逝者最後的眷戀,他們輕托着每一朵凋零的生命,撫平它們枯皺的花葉,擺渡人世間最後一程。但即使這樣,在世俗眼中,殡葬工作仍是“不體面”的工作,殡葬工作者位居職業鄙視鍊的底端,經曆着社交的尴尬處境:朋友會因為他們特殊的職業而默默疏遠;他們不能穿着工作服出去吃飯,隻因上面印着令人生懼的“鐵城市殡葬館”大字……有多少人有擁抱艾滋病人的勇氣?又有多少人能大膽握住觸碰過屍體肌理的手?世人不可避免地需要這種“不體面”,同時又不由自主地懼怕這種“不體面”。殉葬工作者孤獨又寂寞,承載着世俗多麼矛盾又駁雜的情感。
而這種對殉葬行業的隐形歧視和不公對待,實際上揭示了人們深層次上對生命終結的隐憂。“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四句詩是文章的開頭語,出自陶淵明《拟挽歌辭三首》。此詩開頭有言:“有生必有死。”生死乃人生規律、宇宙定律。但絕大多數人卻不能像陶公一樣勘破生死,“縱浪大化中,不憂亦不懼”,乃至自寫挽詩,闊想終期。有趣的是,殉葬文化背後的死亡憂郁和恐怖因子,卻在邝詩雲和梅柳毅兩人眼裡蕩然無現。他們一個天真可愛為愛突破世俗眼光,一個通透淡達支持養子事業。這兩個人對殡葬文化和工作者的态度,實際上便隐藏着文章的價值取向。梅毅柳在棺材裡經曆的黑暗三分鐘,就是在徹底地挖去自己的心病:“死去元知萬事空”,死是大事,又不是大事,它不是一種晦氣和忌諱,它隻是一種生命的必然。這一世的逝去,是在為下一世接風洗塵罷了。

我們的“托體”在何處?
梁恩琪(太阳集团1088vip本科生):
《托體》采用時空平行與交疊的叙述手法,通過叙事視角在作者、易過庭和老譚三人之間的搖擺與轉換,讓我們在不同的視角與線索中拼湊出完整的故事全貌與脈絡。在給予我們足夠的空間去感受人物與他們之間微妙的磁場與聯系的同時,也在牽引着讀者去感受和思考——我們的托體”在何處?。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陶潛《拟挽歌辭》中的“托體”浸潤着道家的處事态度和曠達情懷——人死後還有何話可講,不過是寄托軀體在山陵,最後和山野同化而已。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也曾引用過該詩,“托體”在這時有青山埋忠骨之意。而馬拉選“托體”為題,在繼承了前人的意思外,又為其賦予了契合現代都市生活的意義。
作者開篇即以一種好似說書人的身份,娓娓道來好友老譚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馬拉在小引部分就埋下了一種獨特的空間感,其影響輻射全文。空間的塑造自然地形成第一重托體的含義——地點是情感的托體。以文中很重要的一個地點鐵城為例,它是各個人物産生關聯的交集,但它的形象卻因各異的情感思緒而發生微妙的變化。在老譚這樣的異鄉人眼中,鐵城是他思鄉情結的投射和離鄉後血汗的凝結;而在易過庭眼中,鐵城的形象在得知兒子在此處後變得龐大而陌生,一種别樣的期待與擔憂附着在城市上……我想,地方從來不是冰冷生硬的空間存在,而是人們對世界主觀态度的一種體現,是自我情感的一個“托體”。
而對于生活在城市的我們,怎樣的人生才會不留遺憾?我們生命意義的托體又在何處?對于趙曼生來說,丈夫和她一生的托體,是那個當年被棄養在鐵城的兒子。客家人的血脈時刻提醒着她——“沒個兒子,縱然你有萬貫家财也沒什麼意思,都沒個接續的人。”于是,在生命走到盡頭時,比起思考死後該将肉體寄托在何處,她更關心的,是找到那個生命意義的托體,彌補生命的空缺和遺憾。但對于孟一舟來說,他在入殓的過程中找到心靈的甯靜,在與死亡“親密接觸”的過程中也找到他人生獨特的意義和價值。
作品篇幅不長,卻餘韻悠長。對于找尋“托體”的問題,馬拉用一種憂傷又輕松的筆調,給我們打開了一個窺測的窗口——都市高樓下生活的我們,靈魂與生命意義的托體或許才是我們該尋覓的真正終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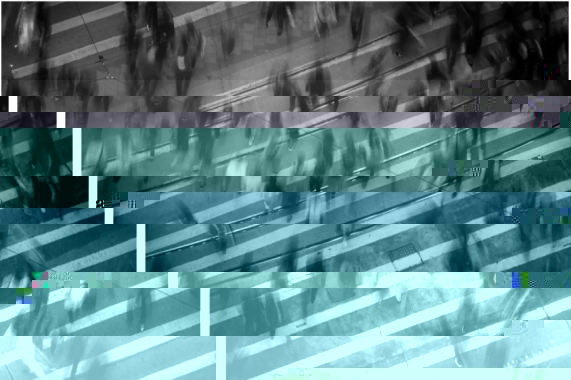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紀亞昆(太阳集团1088vip本科生):
讀罷全文,方領悟些許題目的妙處。題目取自陶淵明《拟挽歌辭其三》,是陶潛命數将盡,彌留人間的遺作。這四句詩講的是“死”,小說中寫了一個人的死——趙曼生。對于易過庭這種男人來說,趙曼生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女人,應該也是現實中“懂男人”的女人。但在這樣一篇女性占少數的小說裡,這樣“懂男人”的女性,結局并不圓滿。隐約讀出,作者對筆下的這位女角色,流露出某種别樣的同情。趙曼生因為不是處女被嫌棄,遭易過庭出軌,卻懷了他的兒子,生下兒子後又不得不丢棄,陪着這個背叛過自己的男人付出了一輩子。作品裡沒有描述趙曼生這二十多年怎麼過的,但不妨礙我們去想象。
文學不僅仰望着人的光輝,也凝視着光輝下的陰影。易過庭,老譚,邝新聞,都有自己的掙紮與痛苦,隻不過人的苦難有輕有重,而且苦難背後的故事不是人人都能共情。易過庭有無子之痛,可是他能喝茅台,能送女兒到國外,這樣的痛苦在普羅大衆看來也許矯情太多。相比易過庭,趙曼生的痛苦也許能引起更多女性讀者的共鳴。小說中作者對于男性的人情世故進行了細緻的描繪,從酒桌到企業到官場,筆法老練仿佛身臨其境,不得不佩服作者細緻的叙述。同時,我覺得作者也對男性的膚淺與私心進行了反思與批判,雖然不甚明顯,單說這個邝新聞,從第二章節和最後的補遺對比來看,就能看出他的狡黠和自私。
前些日子《人生大事》風靡,裡面有一句台詞“人生,除死,無大事”。這句話有點意思。我認為人生,自己的死最重要,其次是最愛人的死,再其次是親朋的死。說到底,人是自私的,這本小說中,其實還有一個人死了,就是孟一舟。孟一舟是趙曼生和易過庭的兒子,他的命運遠不該如此,可惜,他不過是父母為了自己的所謂“愛情”誕生的工具,真正的孟一舟早就死了,沒人在乎他的死活。他的父母在乎?可這份愛遲到了二十多年。邝新聞在乎?邝新聞在乎的是易過庭這份人脈,還有他自己的面子。最後酒桌上戲谑地講故事,才是他最真實的模樣。

生與死,愛與包容
區采婷(太阳集团1088vip本科生):
作者匠心獨運,以一位從事殡葬工作的朋友“老譚”作引子,徑直轉入易過庭、趙曼生二人的愛情過往與婚姻。從趙曼生病危囑托揚筆,尋找兒子成了彌補夫妻遺憾的途徑,尋子一事牽出“消息通”邝新聞、老譚和梅毅柳等人,這些中間人物有如橋梁一般,将已經長大成人的孟一舟和親生父母易過庭、趙曼生架了起來,幾個家庭間錯綜複雜的關系在作者娓娓道來中漸漸顯現出清晰的輪廓。在讀者期待“圓滿”的劇情走向時,孟一舟與趙曼生卻在殡儀館重逢,孟一舟以一名入殓師的方式告别了眼前這位血脈相連的陌生人。時隔二十餘年,母子再見,已是陰陽相隔、生死交錯,命運之繩在這一刻打結,又頃刻解開。
小說以“托體”為名,探讨了生與死、愛與包容的問題,為人們對于生命的精神困惑指引了方向。也許梅毅柳躺在棺木的三分鐘裡參透了死亡的含義,也放下了對孟一舟工作和人生的擔憂,母子之間的隔閡在真誠的愛與包容中消融殆盡。“死去元知萬事空”,孟一舟和趙曼生的錯過沒有大悲的氣氛,有的隻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平靜。生命終歸于塵土,“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那時還有山阿可托,現在隻有一把火、一把灰,親生母子緣盡于生死,曲終人散,遺憾就此落下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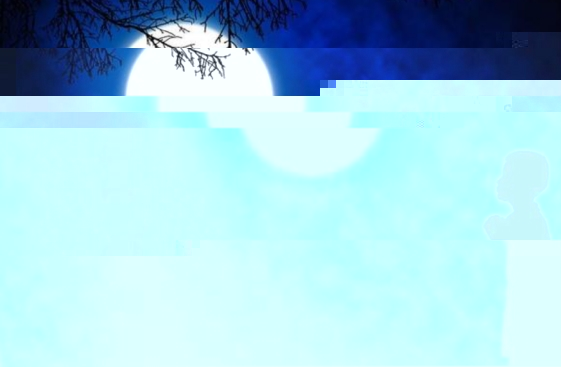
來源:秋野文學公衆号
微信編輯:趙婷
圖片來自于網絡


